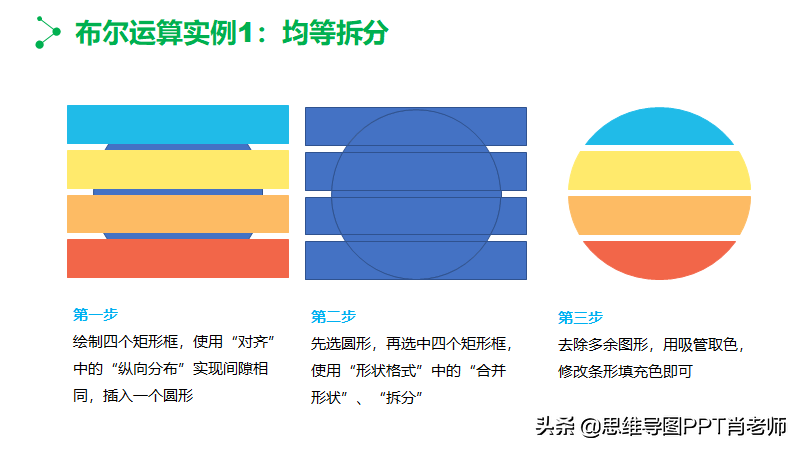前几天在家和母亲闲聊,不知怎的就聊到了我的签名上。母亲说她实在想不明白,就凭我那一把狗出的烂字,竟也敢在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,人家编辑也真是瞎了眼了。
‘一把狗出的’是从小到大母亲对我字体的昵称,我是根据发音打出来的,究竟是不是这几个字也无从考究,总之是贬义词无疑。
面对诋毁,我尽量用平心静气地告诉母亲,现在发表文章都兴往人家编辑邮箱里发送电子邮件,全是电脑打印的。要楷体有楷体,要仿宋有仿宋,一气儿的溜光水滑,不花邮资还不费半点墨水。
七十多岁的母亲当然不会明白电子邮箱是咋回事,但有一点她的确听明白了,即现在发表文章只关乎你的文笔和思想,字写的再好也是白搭,两者基本不会再有半毛钱的关系。
搞不明白是先天就没天赋还是后天不曾努力,总之从开始练描红到使用派克、原子笔,我的那字就从来没有好看过。虽然不像母亲骂的‘一把狗出的’那么夸张,可连我自己都看不过眼确是事实。
上学时父母隔三差五就劝我一定要将自己那笔字练好,否则老那么寒碜,将来到谁单位上班谁不嫌弃。把我说得烦了,就回之以班上姚同学的故事。
这姚同学跟我从小学就在一班,偏好体育运动,文化成绩是一踏糊涂。上课时老师讲的反正也听不懂,姚同学于是就兢兢业业地趴在桌上练字。久而久之,这家伙竟然练成班里一等一的漂亮字,谁见了都得夸几声。但他的学习仍然一落千丈,除了体育和那一笔好字,似乎并没啥可以提起的。
综上所述,学习好的都认真听讲,字写的都不咋样,只有不好好学习的才有时间瞎练出一把好字!虽然是一番邪门歪理,但显然还是颇具说服力,父母生怕我跟姚同学一样不听课光趴桌子练字,从此再不敢劝我,说好坏由它去吧!
大学一毕业,我们单位人事部门负责大学生招聘的是一位姓钟的女士。钟老师平易近人、为人和善,很为我们这帮大学毕业生所尊重。尤其是钟老师写的一笔好字,虽说也论不上什么体,但胜在整齐飘逸,一看就知道是爱干净人漂亮的女士所为。后来,听其他同事说,钟老师学历并不高,以前就在车间里工作。后来经常往单位书写报表,这一手好字被领导相中,于是才上调人事部门工作。
刚刚从大学毕业的学生书卷气未消,天真地以为字好前途就会好,于是几个分配不太理想的同学就开始打字体的主意,天天晚上照着字帖猛练,妄图复制钟老师的童话。
正当大家的字体刚练得有点起色之时,我们单位开始普及推广电脑办公,规定所有的公文全部由WORD书写,打印完毕呈送。不得已,这场刚刚兴起还没轰轰烈烈的练字运动便胎死腹中,后来更成为大家茶余饭后的笑谈。
此后很多年,借助于电脑这一新生事物,字写得很烂这一短板,被我像小狗尾巴一样巧妙地夹藏了起来。除了在庭审之后在笔录上签名之外,我基本上就没动过笔。偶尔没办法写了三行五行的,手腕就像灌了铅一样沉重,比打几场乒乓球都累。
某天跟一以书法见长的朋友喝酒,喝到最后他是长吁短叹。问了半天才知道,原来已经有很多日子没人向他求字了,心里憋屈得慌。该朋友把这一切都归罪于电脑,理由是:一手好字被电脑给废了;一首好拳被骰子给废了;一个好胃被酒给废了;一个好家庭被第三者给废了。我当时同样喝得有点过,书法家朋友刚说出第一句了,我就当即给了他一个响亮的叫好。结果闹得全场愕然,书法家更是差点跟我老拳相向。
前不久本地本地某公众号刊登一篇微信,名字叫“那些手写的书信,被岁月遗忘在了哪个角落 ”。信中怀念了过去我们手写书信的温馨岁月,似乎在不知不觉间,我们都忘了如何在纸上写下一句句的问候和暖人心扉的语句。冷冰冰的电脑代替了充满古风的信封,方方正正的方块字替代了各种颜色的字迹带来的问候。
瞬间,无比煽情的文字激起了我想要手写一封书信的强烈愿望。搜索好半天,才在办公室的角落里找到一只碳素笔,犹豫再三,终于落笔写了起来。刚写了半页纸,自己不禁连皱眉带咧嘴,实在不忍心继续写下去,更遑论将其交付邮差发送远方了。
无奈,只得一片片将信纸撕碎,动作之迟缓、表情之沉痛,仿佛一起扔到废纸篓的还有过去那留也留不住的温馨岁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