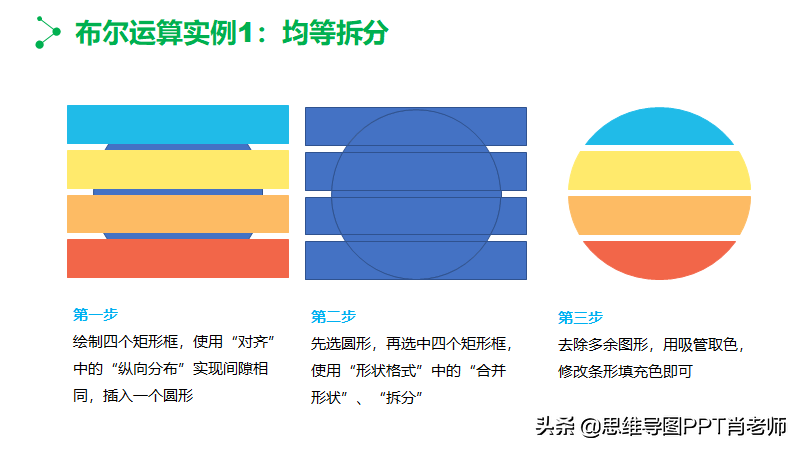名家也有手抖的时候。
我觉得,王蒙先生画《竹石图》的时候,如果没有手抖,那就是手生了。
(王蒙《竹石图》,元代,江苏苏州博物馆藏)
王蒙这人在绘画史上地位极高,与黄公望平起平坐,乃元四家之一,是元代数一数二的山水画家,学他画风的人多如牛毛。
可是见到《竹石图》,我第一感觉是:画山水的跑去画竹子,果然欠火候。
首先,竹叶姿态缺少变化,每一簇长得差不多:
其次,竹叶是竹叶,竹枝是竹枝,竹叶不像是从竹枝上自然生长出来的,彼此间缺乏逻辑关系:
再次,墨色浓淡不明显,竹叶分不清前后关系,没有纵深感:
你再看其他画竹“专业户”的作品,对比之下,伤害更大。
同样是元朝人,人家的竹子就变化无穷,风情万种:
(赵原《墨竹图》局部,元末明初,选自《七君子图》,苏州博物馆藏)
人家把竹叶与竹枝的关系,交代得一清二楚:
(柯九思《墨竹图》局部,元代,选自《七君子图》,苏州博物馆藏)
人家墨色变化丰富,浓淡明显,哪竿竹子在前排,哪竿竹子在后排,一望便知:
(赵天裕《墨竹图》局部,元代,选自《七君子图》,苏州博物馆藏)
有人说,你是不是收了黄公望的钱,故意说王蒙画得不好?
怎么可能!王蒙是一等一的山水画大师,见到他的山水画,如同见到气势磅礴的真山真水,谁会说他画得不好?
(王蒙《青卞隐居图》,元代,上海博物馆藏)
王大师的功力,从《竹石图》里的石头,就能看出来:
画石头果然是山水“专业户”的看家本领。
简简单单几块石头,墨色却异常丰富,干湿并用,浓淡并举,画出了体积感,画出了苔痕斑斑的野趣。
烂竹子配上好石头,这算烂画还是好画?
要说姜还是老的辣。为了把一幅非烂非好的画,变成一幅妥妥的好画,王蒙用了一个特别简单的方法:
他不仅题了诗,而且诗兴大发,一下子题了四首:
一、太湖秋霁画图开,天尽烟帆片片来。
见说西施归去后,捧心还上越王台。
二、西施绝代不堪招,独倚危阑吹洞箫。
七十二峰烟浪里,不知何处是夫椒。
三、夫椒山与洞庭连,半没苍波半入烟。
堪信鸱夷载西子,馆娃宫在五湖边。
四、云拥空山万木秋,故宫何在水东流。
高台不称西施意,却向烟波弄钓舟。
我知道,王大师写了这么好的诗,你们手指轻轻一划,就略过去了,一定没有认真拜读。
其实,只要稍稍了解诗中的人名和地名,就能轻松理解诗意。诗中提到的典故,比如吴越争霸和西施美人,大家从小就听过:
一、太湖秋霁画图开,天尽烟帆片片来。(太湖是中国五大淡水湖之一,靠近吴国故都江苏苏州)
见说西施归去后,捧心还上越王台。(越王台位于越国故都浙江绍兴)
二、西施绝代不堪招,独倚危阑吹洞箫。
七十二峰烟浪里,不知何处是夫椒。(七十二峰指太湖内外的群山;夫椒山位于太湖内,是吴王夫差大败越军的地方)
三、夫椒山与洞庭连,半没苍波半入烟。(洞庭可能指太湖里的洞山和庭山)
堪信鸱夷载西子,馆娃宫在五湖边。(范蠡自号鸱夷子;馆娃宫是吴王夫差为西施修建的宫苑;五湖是太湖的别称)
四、云拥空山万木秋,故宫何在水东流。(故宫与现在的北京故宫无关,应指曾经的吴国宫殿)
高台不称西施意,却向烟波弄钓舟。(高台可能指吴王夫差用于享乐的姑苏台)
值得一提的是“馆娃宫”这个地名。馆娃宫是吴王夫差专为西施修建的离宫别苑,据说位于苏州西郊灵岩山。
灵岩山至今仍然保留了一些馆娃宫遗迹,比如所谓的吴王井和梳妆台。当然,吃货去那里玩,更关心山上庙里的一碗素面。
(图片来自网络)
这时,你再读王蒙写在诗后的一段话,便什么都懂了:
(至正甲辰九月五日,余适游灵岩归,德机忽持此纸命画竹,遂写近作四绝于上,黄鹤山人王蒙书)
王蒙说,我在灵岩山玩了一圈,回来碰上张德机(元代收藏家)。小张带了好纸过来,求我画一幅竹子,我就顺便把最近创作的四首绝句题了上去。
综合以上信息,我们终于可以大致还原出事情的经过。
张德机是王蒙好友,敬佩王蒙的画技,这天特意请他画一幅竹子。为何点名要竹子?文人以君子为做人准绳,而竹子虚心有节,乃梅兰竹菊“四君子”之一。请朋友画竹子,无非是说“你这样性情高洁的君子才能画好竹子”,或者“我这样性情高洁的君子才配欣赏竹子”。
还有一种可能性是,画竹子比较快。可能张德机急不可耐要拿回家挂起来(因为题跋中没有提到第三个人,所以这幅画应该不是张德机拿来送人的),也可能王蒙很快要去外地,画山水来不及,而竹子仅需寥寥数笔,立等可取。
王蒙与张德机估计相当熟络,人家请他画竹子,他竟然自说自话题了一堆诗,估计这几首都是王蒙的得意之作。王蒙在苏州只是暂住,玩了一圈周边景点,回想吴越往事、美人心迹,心里生出许多感慨。古人怀古,往往意在讽今,王蒙说不定把个人际遇融在了诗里,只是我没读出来,张德机或能心领神会。
体会了这些,你再看《竹石图》:
是不是感觉有所不同?
这一次,你看到的不仅仅是一幅画了。
你还看到了竹子所代表的文人价值取向,看到了两位文人的交往和友谊,看到了苏州城外千年不绝的怀古幽思。
单单几竿竹子,几块石头,无法让你看到这么多。
你能洞彻画意,靠的是画家题的诗。
(友情出演:蒋兆和《杜甫像》,当代,中国国家博物馆藏)
(友情出演:郎世宁等《乾隆皇帝与后妃像》局部,清代,美国克利夫兰美术馆藏)
最初,古代画家并不习惯在画上题诗。
元代以前的画家不要说题诗了,连签名都少见。即使签了名,也常常签在犄角旮旯,很容易被忽略。
(马远《梅石溪凫图》,画面左下角有“马远”二字,南宋,北京故宫博物院藏)
即使画上有诗,题诗的人也常常不是画家自己,而是“雇主”。
(马麟《层叠冰绡图》(绡音肖),南宋,北京故宫藏)
这幅梅花图是南宋宫廷画家马麟的作品,画上的咏梅诗却是当朝皇后杨氏(宋宁宗皇后)写的,马麟只在右下角签了非常小的“臣马麟”三个字。
如此低调,一是因为当时的画家认为,签名和题诗会破坏画面;二是因为多数画家以画画为生,属于职业“画匠”,主要任务是满足“甲方”的要求。他们可能并不具备扎实的文学功底,而甲方也不希望他们在画上留下太多个人印记。
不过,宋代也出现了一批特殊的画家。他们要么身负官职,要么有田有地,要么皈依佛道,总之不以卖画为主要收入来源。这些人把绘画当作抒发情感、结交朋友的工具,开始用诗歌衬托画意。
但他们题诗的时候,还是尽量不去破坏画面。诗歌与绘画保持着“礼貌的距离”:
(扬无咎《四梅图》局部,南宋,北京故宫藏)
到了元代,时代风气又不一样了。
同样是梅花,元代画家王冕的这幅《墨梅图》就有了新意:
(王冕《墨梅图》,元代,北京故宫藏)
画上两首诗,右边那首是乾隆皇帝后来题的,请无视。
左边这首是王冕自己写的:
王冕写道:吾家洗砚池头树,个个华(花)开淡墨痕。不要人夸好颜色,只流(留)清气满乾坤。(耳熟不?)
光看画,你以为他随便画了枝梅花;读了诗才知道,王冕画的是自家梅树。
他在池塘边清洗砚台,梅树仿佛吸取了墨汁,花瓣上竟有点点印记,宛如斑斑墨痕。虽然花色并不娇艳,但花香沁人心脾,飘散万里,天下皆知——这还是在说梅花吗?显然在说画家本人的高尚品格啊!
《墨梅图》的新意在哪里?在于题诗的位置。
诗歌与梅枝之间不再有“礼貌的距离”,而是呈现穿插之势,彼此呼应,融为一体。
这时,你再回想王蒙的《竹石图》,不禁要赞叹王大师的“创新能力”:他题诗的位置才是最最奇葩的:
一是面积大,题诗直接占去画面的三分之一,与竹子或石头的地盘差不多。
二是位置好,题诗直接霸占画面正中间,生生将一幅绘画,变成了“带插图的书法”。
如果去掉题诗,你会觉得这幅画根本没有画完:
这足以说明,王蒙在动笔画竹子之前,已经盘算好,要预留出四首诗的位置。这种奇葩的构图,完全是他故意设计的。
更奇葩的是,他题的四首诗,与竹石一点关系都没有。
王冕画了梅花,所以歌咏梅花,自比梅花,合情合理。王蒙画了竹石,却在诗里大谈太湖、群山、古迹、美人,没有半句话提到竹子和石头。
他一定是故意的。
可是对前来求画的小张来说,这又有什么关系呢?不仅得到了画作,还读到好友的新诗,两人品茗再三,唱和一二,度过一个美好的下午。
对观众来说,就更是一桩美事了:看看画上的竹子,体味儒家君子的高风亮节;读读画上的题诗,太湖美景仿佛映入眼帘;回想儿时的课本,东施效颦与卧薪尝胆似乎还是考点;兴许你也登过灵岩山,兴许画家也端起过那碗清爽的素面。
眼里是画,心灵却早已飞出画外,进入了元代文人的精神世界。
带给你这番体验的,既是诗,也是画,是诗画合一的中国画。
因为诗的出现,中国画从此大不相同。
【后记】本文属于“闲话”系列,因为凑了三个小主题,都与文人画有关,所以单独取了“文人画三题”这么个文绉绉的系列名称。
说王蒙先生的竹子画得烂,当然是开玩笑。王蒙的可靠真迹存世很少,竹画更是凤毛麟角,把《竹石图》列为苏州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也不为过。
相比其他画竹名家,《竹石图》对竹子的处理,确实略显草率,但这种逸笔草草的风格,倒是很有隐逸之气、潇洒之风,与整幅画的格调很般配。《竹石图》曾是苏州大收藏家顾文彬的藏品,由其后人顾公硕捐献国家。
文/博小拙
微信公众号:王牌讲解员